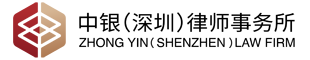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非法集資類犯罪的一種。在當今社會,金融市場融資環境較為復雜,因銀行等金融機構融資條件的嚴苛性與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發展的融資需要存在沖突,刺激了民間私人融資需要的產生。一方是急需資金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民營企業,另一方是手握流動資金尋求投資回報的投資者,供需關系的滿足刺激了雙方之間的合作。
但因融資實踐中操作的不規范、監管不到位等原因,導致正常的金融融資活動突破了合法的界限。且其自身因經營不善等原因導致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投資者投資款項,導致投資者遭受巨大經濟損失,對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壞,從而致使正常的金融融資活動演變成非法集資活動。面對這種情況,為維護金融管理秩序的穩定性、保障投資者的合法財產權利,有必要用刑事法律對金融融資活動進行規范和約束,使其不突破正常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為進一步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正常融資活動之間的界限、明確司法審判依據和司法實踐中的操作指引,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相關的司法解釋,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非法集資類犯罪制定了更加明確具體的定罪量刑的標準,提出了“四性”特征,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包括單位和個人)吸收資金的行為,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條件的,除刑法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一)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二)通過網絡、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信息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四)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該條規定明確提出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需同時滿足上述四個條件。法律規定的進一步細化為司法機關提供了辦案指引,有助于提高其辦案效率,但該規定仍然存在規定不明確、可解釋空間較大的問題,仍然有讓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成為經濟犯罪中“口袋罪”的嫌疑。因此,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性”特征仍有做進一步分析和明確的必要。
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性”特征
(一)非法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首先應當考察行為人的“非法性”,“非法性”是指行為人“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這一規定體現了我國刑法對行為人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范行為的規制。首先,“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主要是針對從事存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這類主體只有經過國家金融管理機構的許可才能從事吸納公眾存款的業務。并非所有的融資活動都需要國家政府部門的特別許可,例如平等主體之間的法人、自然人、以及非法人組織之間基于融資的需要,雙方之間自愿達成協議、成立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由于并未從事存貸款等需要特許經營的金融業務,因此這類屬于正常借貸關系的金融融資活動無須得到金融管理部門的許可,否則,必然會對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的發展造成不必要的阻礙,反而不利于我國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其次,對于“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這一規定較為模糊,上述司法解釋在第二條規定中采用“列舉+概括”的模式對其做了細化規定,即“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符合本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條件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一)不具有房產銷售的真實內容或者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銷售房產份額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二)以轉讓林權并代為管護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三)以代種植(養殖)、租種植(養殖)、聯合種植(養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四)不具有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的真實內容或者不以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購、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五)不具有發行股票、債券的真實內容,以虛假轉讓股權、發售虛構債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實內容,以假借境外基金、發售虛構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七)不具有銷售保險的真實內容,以假冒保險公司、偽造保險單據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八)以網絡借貸、投資入股、虛擬幣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九)以委托理財、融資租賃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十)以提供“養老服務”、投資“養老項目”、銷售“老年產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十一)利用民間“會”“社”等組織非法吸收資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資金的行為。”該規定僅是對實踐中有可能出現的幾種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進行了列舉,并非是窮盡所有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實踐中,借用合法經營形式規避非法集資的手段主要表現為投資基金、項目投資、股權、債權轉讓、商品回購等手段。縱觀上述列舉的多種行為,可以看出認定“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的關鍵是“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掩蓋其融資借貸的目的,在考察相關融資活動是否具有“非法性”時,可以重點關注行為人宣傳的投資項目是否真實存在、是否將募集資金實際投入到所宣傳投資項目的經營中、融資實際用途和融資目的是否一致。如果融資人所宣傳的生產經營項目是真實存在的,也將絕大部分所募集資金都用在該項目的生產經營中,則其融資行為不具有“非法性”的特征。反之,如果行為人所宣傳的融資項目并不真實存在,或者其融資實際用途和融資目的并非一致,則其行為具有“非法性”的特征。
(二)公開性“公開性”是指行為人通過網絡、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信息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進行融資活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所以要求具備“公開性”的要求,是因為“公開性”會導致該罪的社會危害性的擴張,行為人采取向社會公開宣傳的方式進行融資,基于從眾效應,容易導致受害人范圍的擴張,更多的普通投資者會因為輕信這類投資行為具有較高信譽的高收益而進行投資,最后卻因各種原因導致融資人無法及時足額地還款而暴雷,損害了投資人的合法財產權利。這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應,破壞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穩定性,降低民眾對國家金融體系的信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公開性”和“社會性”是緊密聯系的,如果融資人僅是通過私人溝通聯系的方式尋找投資資金,比如通過私人借貸的方式僅在小范圍內進行募資,則其行為沒有這種公開性質的社會危害性,不應當被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此外,在有些情況下,某些投資效益前景較好的投資項目并非是融資人主動尋求投資資金,而是投資者主動找上門想要通過投資獲取日后的豐厚回報,這種情形僅是投資人參與經濟活動自身應當承擔的風險,這一行為不應收到刑法規制。
(三)利誘性“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利誘性”特征。不能僅認為融資人以投資項目可以為投資人帶來高收益進行融資宣傳就認定其行為具有“利誘性”。一般的投資活動必然是以賺取投資項目產生的利潤或者收益為目的的,而融資人在宣傳其融資項目時必然也會描繪該項目具有較好的投資收益前景,但投資行為的最大特點還是其獲得收益的不確定性、具有虧損“風險”這一特征。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利誘性”要求規制的是那些承諾可以“保本”且可以收獲高額回報的融資行為,這種“還本付息”的承諾帶有誘騙性質,若對這種帶有誘騙性質的融資行為不加以規制,勢必會對正常的金融機構的存貸款業務造成沖擊。支付合理利息或者回報的正常民間借貸行為或者正常融資行為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而非法集資行為由于承諾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償還本金并支付超過一般投資回報利率的利息,導致其具有誘騙性、投機性,行為人此時的許諾僅是為了誘使投資者投資資金,以解決自己資金短缺的問題,但事實上對于還本付息的承諾是否具有現實能力的支撐是不確定的,這也是其受到刑法規制的原因。
(四)社會性“社會性”是指行為人具有“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這一行為。對于“社會不特定對象”這一較為不明確的表述,司法解釋采取了以人數或者金額來界定“特定”和“不特定”的方法,即要求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達到一定數量或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金額或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達到一定數額的,才對行為人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進行定罪處罰,而這一因素也是對行為人進行量刑的重要標準。要求吸收人數較多的存款人這一條件似乎能夠符合“社會不特定對象”這一條件,但如前所述,該罪名的“社會性”和“公開性”是緊密聯系的,回歸該罪名的立法本意,其本意是保護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穩定性,司法解釋中也明確規定了“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如何認定“社會公眾”問題的解釋,如果行為人是通過一個個私下溝通的方式取得投資資金的,即使投資者人數較多,也不能被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同樣,即便是投資者的投資資金數額或者損失金額巨大,在投資人數較少且也沒有采取公開宣傳的情況下,該行為也不應當被認定為成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三、司法案例及辯護思路
【案例一】宛龍檢公訴刑不訴〔2018〕12號基本案情:2013年底,楊某某的前夫陳某某與趙某某經營某酒店,楊某某籌集資金430萬元借給趙某某,趙某某給楊某某出具了借據。其中,楊某某以本人名義向親戚、朋友、同學及親友的親朋共17人出具了借條,借款190萬元,借條上未約定利息,但楊某某按雙方口頭約定月息1分5實際支付了利息。另外,楊某某以某公司的名義向親戚、親戚的朋友等5人出具承諾函借款74萬元,約定月利率千分之十五。經查,該承諾函上借款擔保的公司系虛構、加蓋的公章來源現無法查明,但楊某某借款后按期支付利息至2015年7、8月份,因酒店經營不善,趙某某未還款,余款楊某某也無力償還。案發后,楊某某已歸還大部分人的全部借款,歸還了其余受害人的部分借款、對于剩余借款已經達成還款協議,其余一人的借款未歸還但法院已經作出生效民事判決并已進入了執行程序,最終檢察院對楊某某作出不起訴決定。【辯護思路】對于楊某某的行為,根據前文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四性”特征的分析,雖然其采取了虛構公章的方式為借款提供擔保,但其行為并不符合前述的“四性”特征。首先,楊某某并沒有采取公開宣傳的方式向社會募集資金,其募集資金的對象也不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相反,其募集對象滿足司法解釋規定的出罪條件“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其次,楊某某的經營項目是真實存在的,也將所募集的資金主要投入到該項目的實際經營中,后來無法及時還款也是因為酒店經營不善導致,楊某某并不具有非法占有投資人存款的目的,其借款行為屬于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不構成犯罪。再次,楊某某在案發后提起公訴前已經歸還大部分借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楊某某的行為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案例二】(2013)黃浦刑初字第1008號基本案情: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間,被告人吳某身為被告單位上海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負責人,以該公司投資或者經營需要資金周轉為由,承諾高額借款利息為誘,部分提供房產抵押或珠寶質押,通過出具借據或簽訂借款協議等方式,非法向涂某某等人吸收存款,共計人民幣15,460萬元。最終法院判決被告人吳某和被告單位上海某有限公司均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辯護思路】1、吳某的行為不具有“公開性”,其沒有采取公開宣傳的方式向社會募集資金。從宣傳手段上看,吳某借款方式為或當面或通過電話一對一向借款人提出借款,并約定利息和期限,既不存在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的情形,亦無證據顯示其要求借款對象為其募集、吸收資金或明知他人將其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2、吳某的借款對象范圍相對封閉,不符合“社會性”的要求。從借款對象上看,吳某的借款對象絕大部分與其有特定的社會關系基礎,范圍相對固定、封閉,不具有開放性,并非隨機選擇或者隨時可能變化的不特定對象。對于查明的出資中確有部分資金并非親友自有而系轉借而來的情況,但現有證據難以認定吳某系明知親友向他人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此外,其個別親友轉借的對象亦是個別特定對象,而非社會公眾;3、吳某并沒有采取許諾以高額回報的方式誘使借款人借款,不符合“利誘性”的特征。吳某在向他人借款的過程中,存在并未約定利息或回報的情況,對部分借款還提供了房產、珠寶抵押,吳某的借款行為不具有誘騙性和投機性,故吳某的上述行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
【案例三】京海檢公訴刑不訴(2018)150號基本案情:2013年以來,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以理財產品的名義和有限合伙人投資入股的方式,進行公開推介與資金募集,向社會公眾、不特定的對象吸收公眾存款,涉案人數70余人,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檢察院最終以周某某的行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性”特征為由,對周某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辯護思路】周某某在進行融資活動時雖然存在對投資項目收益情況的一個表述,但該表述僅是融資活動中正常的對融資項目預期收益情況的表述,且其在融資時已經對投資項目進行了相應的風險提示行為,也不具有“還本付息”的承諾,因此其行為不符合“利誘性”的特征,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檢察院觀點如下所示:首先,本案投資人簽訂的合同中,不存在“還本付息”的相關內容,對于預期年化收益率的表述只是為了確定如果盈利后返利的標準。退一步講,如果說這一表述還不太明確,但在同一份合同中列明了風險提示,也可以說明周某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并不是做出“還本付息”的承諾。而且,除合同外周某某還與投資人簽署了風險確認函,更能說明問題。其次,在本案中周某某并未與投資人直接接觸,故投資人無法指認其行為,而林某某作為唯一的中間人也沒有指認周某某要求其進行“還本付息”相關的宣傳,故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某某的行為具備“利誘性”的特點。綜上,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應當立足其立法原意,行為人的行為必須同時滿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這四個特征,才能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否則,基于刑法的謙抑性和為保障融資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考慮,行為人的正常融資行為不應當受到刑法規制。在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制定辯護策略時,應當根據其“四性”特征,從行為人的行為不能同時滿足這四個條件進行突破,為犯罪嫌疑人制定相應的無罪辯護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