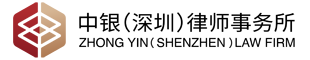“司法解釋每個條款背后都至少有一個典型案例”
糧安天下,種筑基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項技術能夠創造一個奇跡”,“十幾億人口要吃飯,這是我國最大的國情,要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下決心把民族種業搞上去,抓緊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從源頭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而強化植物新品種保護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支撐,因此2021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企求進一步優化種業營商環境。作為在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實踐耕耘近十五年的老兵,第一時間對該征求意見稿進行學習并點評。
01【共有權行使】
第一條 【共有權行使】 植物新品種權(以下簡稱品種權)的共有人對品種權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任一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品種權。
共有人之一單獨實施該品種權,其他共有人主張該實施收益在共有人之間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共有人之一許可他人實施該品種權,其他共有人主張收取的許可費在共有人之間分配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點評:《種子法》第73條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39條均規定,品種權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對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直接提起訴訟。但實踐中對于共有和轉讓情形下誰可以提起侵權訴訟,仍有爭議。我國《種子法》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并沒有像《專利法》明確規定共有人的權利行使規則,[1]故為了避免實踐中對品種權共有人的許可權和訴訟權產生爭議,遂有該條共有權行使規則的意見:共有人對品種權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任一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品種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按照反對解釋,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是不能以排他許可或獨占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的。以(2014)民申字第52號案[2]為例,最高院認為,本案中,“吉祥1號”的品種權人為武威農科院和黃文龍,雖然雙方的轉讓行為因沒能登記公告而未發生法律效力,但雙方約定由武威農科院單獨行使植物新品種權的意思表示真實合法有效。作為品種權的共有人武威農科院,其亦有權單獨實施或者以其他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吉祥1號”品種權。
02【受讓人原告資格】
對于第二款前一句,共有人之一單獨實施該品種權,其他共有人主張該實施收益在共有人之間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筆者認為,此句中共有人應限于“合意共有”的情形,不適用于并非相關主體合意而形成的共有。以品種權權屬糾紛為例,尚未離職的育種人員私下為競爭企業工作并以競爭企業申請品種權,后經法院審理認為兩企業均對申請的品種權作出了實質性貢獻,確認所申請的品種權歸雙方共有。在判決之前競爭企業已經自行實施該專利并獲益較大的情形下,如果一概不予支持判決的實際共有人參與分配,似有違公平。
第二條 【受讓人原告資格】 品種權轉讓未經國務院農業、林業主管部門登記公告,受讓人以自己名義提起侵害品種權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點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9條第4款規定,轉讓申請權或者品種權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并向審批機關登記,由審批機關予以公告。可見,植物新品種權的審查和授予是國務院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利,該權利的存在與否,期限長短以及歸屬均由該行政審批機關負責登記。著錄事項變更登記雖然是一種行政管理措施,但其涉及合權利人利益的同時,也涉及公眾的利益,植物新品種的變動應當進行公示以具有權利外觀。
因此,品種權沒有進行登記公示之前,品種權轉讓行為并未生效。以(2014)民申字第53號案[3]為例,最高院認為,不論本案是否存在敦煌種業公司所稱的“吉祥1號”品種權因被依法凍結而不能進行著錄項目變更的情況,黃文龍與武威農科院之間的植物新品種轉讓未完成變更登記公告是客觀事實,故“吉祥1號”品種權轉讓行為尚未生效,尚不能認定武威農科院是涉案品種“吉祥1號”唯一的品種權人,敦煌種業公司關于品種權是否登記并不影響品種權共有人轉讓品種權的申請再審理由,不予支持。
03【繁殖材料】
第三條 【繁殖材料】 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包括該品種的繁殖材料。該繁殖材料應當具有繁殖能力,且繁殖出的新個體與該授權品種的特征、特性相同。前款所稱繁殖材料不限于以申請品種權時所采用的培育方式獲得的繁殖材料。點評:長期以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在理論界抑或是實務界,品種權保護范圍均存在爭議,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國際上,有觀點認為,收獲材料(包括使用繁殖材料獲得的整株植物和植物的部分),植物本身以及為嫁接和繁殖新植物而被切斷的枝條、接穗,都應當作為繁殖材料給予保護;也有觀點認為,應包括植物的任何材料等。而UPOV公約78 文本中將品種權的保護范圍限定在“有性或無性繁殖材料”和“無性繁殖材料應包括植物整株”兩個方面。 [4]UPOV公約91文本則將由繁殖材料延伸至了收獲材料及直接制成品。[5]而在國內,則有觀點認為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界定涉及科學技術理論問題,不是司法機關單獨所能解決的,但就某些記載新品種特異性的授權機關的書面審査材料,在與授權機關達成共識后,最高院可以先行解釋作為侵權判定的證據使用[6]。 還有觀點認為,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應當是授權品種的特異性[7]。《司法解釋一》征求意見時,林業和農業的主管部門也有不同意見,前者認為應以審批機關批準的品種權申請文件記載的特異性為保護范圍,而后者則主張申請品種的全部遺傳特性都包含在繁殖材料中,應以繁殖材料來確定品種權保護范圍。[8]《司法解釋一》初稿也曾經基于專利權與品種權最為接近的考慮,擬借鑒專利侵權的認定方法,但因植物品種是活體,以繁殖材料為載體的生物遺傳特性難以用文字全面、準確地描述,無法采用專利侵權判定的“三步走”方法。 [9]《司法解釋一》最終以被控侵權繁殖材料與授權品種具有相同特征特性作為比對標準進行侵權認定,而并未直接規定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是什么[10]。《司法解釋二(意見稿)》明確將繁殖材料作為我國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筆者認為,繁殖材料包括有性繁殖材料和無性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種權所指的繁殖材料涉及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應當以品種權法律制度為基礎進行分析。在(2019)最高法知民終14號案[11]中,最高院認為判斷是否為某一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在生物學上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其屬于活體,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個體與該授權品種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訴侵權蜜柚果實是否為三紅蜜柚品種的繁殖材料,不僅需要判斷該果實是否具有繁殖能力,還需要判斷該果實繁殖出的新個體是否具有果面顏色暗紅、果肉顏色紫、白皮層顏色粉紅的形態特征,如果不具有該授權品種的特征特性,則不屬于三紅蜜柚品種權所保護的繁殖材料。本條第二款明確繁殖材料的范圍在授權后可以有變動,讓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通過繁殖材料全面保護授權品種。正如在上述案件中,雖然蔡新光在申請三紅蜜柚植物新品種權時提交的是采用以嫁接方式獲得的繁殖材料枝條,但并不意味著三紅蜜柚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僅包括以嫁接方式獲得的該繁殖材料,以其他方式獲得的枝條也屬于該品種的繁殖材料。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同于植物新品種權授權階段繁殖材料的植物體可能成為育種者普遍選用的種植材料,即除枝條以外的其他種植材料也可能被育種者們普遍使用,在此情況下,該種植材料作為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應當納入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12]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界定繁殖材料的范圍時,品種實際栽培時采用的與產品定價相符的常規繁殖技術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使用特殊的繁殖方式,比如采用組培、細胞培養等手段時,其成本是否能夠支撐商品利潤,是否能夠在實際生產中大范圍應用,也是繁殖材料的范圍界定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13]。
04【許諾銷售】
第四條【許諾銷售】 以廣告、展陳等方式作出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銷售行為認定處理。
點評:早在(2017)最高法民申4999號案[14],最高院明確,許諾銷售是否是侵權行為的問題應該與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保持協調。《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1978年文本)第5條第1款規定:授予育種者權利的效果是在對受保護品種自身的有性或無性繁殖材料進行下列處理時,應事先征得育種者同意:以商業銷售為目的之生產;許諾銷售;市場銷售。根據國際法與國內法解釋一致性原則,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六條所稱的“銷售”應該包括許諾銷售行為,而本條文則是直接明確許諾銷售行為的屬性。實踐中,許諾銷售時往往以品種名稱向公眾進行展示,且侵權人為規避風險,也多選擇將繁殖材料隱蔽處理。將“以廣告、展陳等方式作出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納入銷售行為處理,有助于打擊侵害品種權的銷售行為。
05【種植行為】
第五條【種植行為】 種植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以生產、繁殖行為認定處理。
點評:本條文似可以消除筆者之前對(2018)最高法民再290號案[15]的困惑,(2018)最高法民再290號案中,最高院認為,京秦管理處的被訴侵權行為是,在其管理的高速公路兩側及綠化帶種植使用未經授權的美人榆苗木的行為。雖然涉案美人榆為無性繁殖品種,其植株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但是,根據本案現有證據,以及法潤公司在庭審中關于“京秦管理處無擴繁行為”這一事實的認可,無證據顯示京秦管理處種植涉案美人榆苗木是為了銷售營利,且其并未實施扦插、嫁接等擴繁行為,在此情況下,種植行為本身既不屬于生產行為,也不屬于繁殖行為。但在本條文的釋義之下,被告的種植行為或許可以認定為侵權行為。
06【相同推定和假冒品種】
第六條【相同推定和假冒品種】 品種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以下合稱權利人)舉證證明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稱與授權品種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該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屬于授權品種繁殖材料;有相反證據證明不屬于該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被訴侵權人構成假冒品種權行為,并參照假冒專利行為的有關規定處理。
點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18條第1款規定植物新品種應當與相同或者相近的植物屬或者種中已知品種的名稱相區別。早在(2017)最高法民申4993號案[16]中,最高院明確,授權品種的名稱具有獨特性,在沒有相反證據時,名稱相同的品種可推定為同一品種。而且,根據該案植物新品種請求書的說明書部分關于“雙季米槐”特性的記載及雙季槐專刊對“雙季槐”特性的記載,兩者具有類似的特性。因此,基于本案原審現有證據,可以認定雷茂端、茂端種植合作社對外推銷的繁殖材料為“雙季米槐”的可能性較大,達到了高度蓋然性的證明尺度。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基于現有證據認定相關事實成立。雷茂端、茂端種植合作社并未提供相應的反駁證據,應認定其推銷的對象為授權品種“雙季米槐”繁殖材料。
本條文后段直接回應假冒品種權的問題,讓侵犯品種權的行為“無所遁形”。此前《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40條和《種子法》第73條第6款均規定,假冒授權品種的,可以責令停止假冒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和植物品種繁殖材料。但依據規定內容無法判斷假冒授權品種是否屬于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有觀點認為,假冒授權品種行為屬于欺詐行為甚或生產銷售假劣種子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品種權[17]。 也有觀點認為,假冒品種在市場上銷售,必然有損品種權人的聲譽,進而損害品種權人獲益的權利,這樣的直接侵犯品種權人的名稱標記權益,應屬于廣義侵權行為。[18]在司法實踐中,有直接將銷售假冒授權品種認定侵權行為的做法,如在(2019)皖01民初1055號案中,[19] 法院認為,任何人未經品種權人的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銷售假冒授權品種的種子,即侵犯了品種權人的權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2018)皖民終8號案[20]中,法院認為侵犯植物新品種權和假冒授權品種同樣屬于侵權行為、違法行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司法解釋二(意見稿)》意圖參照假冒專利行為的有關規定處理,但假冒專利所要依法承擔的民事責任中是否必然包含有專利侵權責任仍不明晰,這對假冒植物新品種而言自然也是一個空白。
07【違約與侵權競合】
第七條【違約與侵權競合】 受托人、被許可人超出與品種權人約定的規模或者區域生產、繁殖、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品種權人對此主張構成侵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點評:本條文所指的生產并不純粹指田間的種子生產,超出受托或許可范圍擴繁授權親本材料也是在詞義范圍內。[21]在(2019)最高法知民終]953號案中,最高院明確,植物新品種權人委托他人生產該品種種子并明確限定了生產規模,受托方未經許可擅自銷售超出合同約定規模的種子的,構成對植物新品種權的侵害。需要說明的是,違反約定的銷售形式不一定侵害植物新品種權,如在(2014)民申字第54號案中,[23]最高院明確,經審查,武科公司、赤天公司生產、銷售的被訴侵權“吉祥1號”產品來源于三方協議的約定,根據現有證據無法認定違反三方協議約定的銷售形式就存在未經權利人許可生產、銷售“吉祥1號”的侵害品種權的事實。至于武科公司、赤天公司的行為是否超出了三方協議約定的銷售區域和銷售形式,此爭議在三方協議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應當通過是否違反合同的違約之訴予以解決。
本文引用
1. 《專利法》第15條規定:“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2. 甘肅省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河南省大京九種業有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
3. 甘肅省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河南弘展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
4. UPOV Convention(1978 Act), Article 5.
5. UPOV Convention(1991 Act), Article 14(2).
6. 劉軍生:植物新品種糾紛司法實踐中的若干問題,載《電子知識產權》2004年第10期。
7. 郝力、胡雪瑩: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案件審理的問題,載《人民司法》2005年第1期。
8. 蔣志培、李劍、羅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6年第2輯。
9. 李劍:審理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基本問題辨析,載《人民司法(應用)》2008年第7期。
10. 羅霞: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的相關思考,載《人民司法(應用)》2016年第7期。
11. 蔡新光、廣州市潤平商業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1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5831.html,訪問日期2020年5月25日。
13. 狄強、謝湘:關于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條例中繁殖材料范圍界定的討論,載《科學導報·學術》2019 年第19期。
14. 萊州市永恒國槐研究所、葛燕軍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
15. 河北省高速公路京秦管理處、河北法潤林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
16. 萊州市永恒國槐研究所、雷茂端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
17. 武合講:假冒授權品種不侵犯品種權,載《種子世界》2014年第1期。
18. 李劍: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基本問題辨析,載《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8年第1輯。
19. 北京聯創種業有限公司與王保敏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
20. 江蘇明天種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遠縣山泉農資經營部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21. 萊州市永恒國槐研究所、雷茂端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
22. 武合講:假冒授權品種不侵犯品種權,載《種子世界》2014年第1期。
23. 李劍: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基本問題辨析,載《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8年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