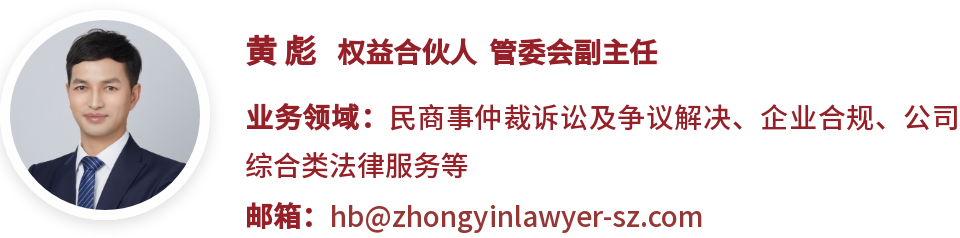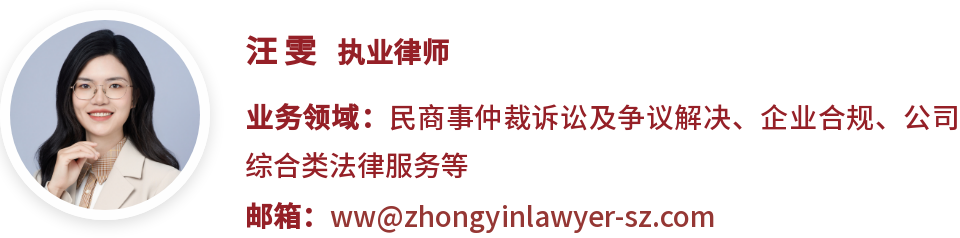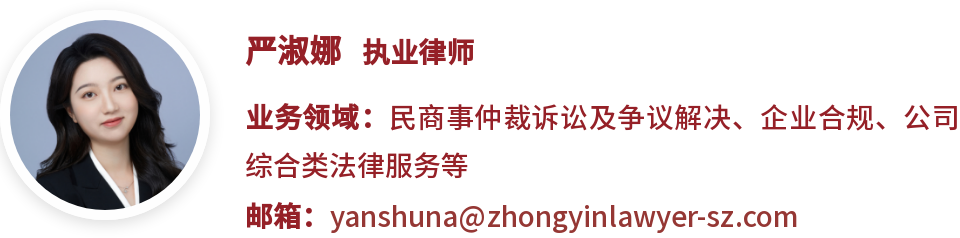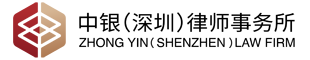引 言
隨著現(xiàn)代科技尤其是信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信息網(wǎng)絡(luò)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為人們進(jìn)行信息交流等提供了線上平臺(tái)。與此同時(shí),區(qū)別于傳統(tǒng)交易方式,以信息網(wǎng)絡(luò)為交易媒介的交易方式也應(yīng)運(yùn)而生。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新增了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訂立買賣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補(bǔ)充規(guī)定。
同時(shí),基于信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高速發(fā)展及其帶來(lái)的巨大便利,通過(guò)淘寶、京東、微信、供應(yīng)商云平臺(tái)等各類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的交易越來(lái)越多,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越來(lái)越多,“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的種類也愈發(fā)具有多樣性,這也導(dǎo)致了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激增。然而,司法實(shí)踐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對(duì)該類案件的管轄認(rèn)定存在不同的觀點(diǎn)。
本文將從傳統(tǒng)交易方式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本文特指常見(jiàn)的、以動(dòng)產(chǎn)為交易對(duì)象的買賣合同糾紛,不包括有特殊管轄規(guī)定的買賣合同糾紛)的地域管轄規(guī)定、“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地域管轄規(guī)定、法律適用規(guī)則等方面對(duì)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問(wèn)題進(jìn)行梳理、探討。
一、傳統(tǒng)交易方式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
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對(duì)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管轄進(jìn)行了明確的規(guī)定,其中又以當(dāng)事人是否有協(xié)議約定管轄作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了區(qū)分。
在當(dāng)事人沒(méi)有約定管轄法院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2023修正)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同時(shí),《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修正)第十八條規(guī)定,“合同約定履行地點(diǎn)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diǎn)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duì)履行地點(diǎn)沒(méi)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zhēng)議標(biāo)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動(dòng)產(chǎn)的,不動(dòng)產(chǎn)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其他標(biāo)的,履行義務(wù)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即時(shí)結(jié)清的合同,交易行為地為合同履行地。合同沒(méi)有實(shí)際履行,當(dāng)事人雙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因此,基于上述規(guī)定,在當(dāng)事人沒(méi)有約定管轄法院的情況下,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
同時(shí),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對(duì)于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民事訴訟法同樣賦予了當(dāng)事人可以協(xié)議選擇一審管轄法院的程序性權(quán)利。《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2023修正)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合同或者其他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糾紛的當(dāng)事人可以書面協(xié)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biāo)的物所在地等與爭(zhēng)議有實(shí)際聯(lián)系的地點(diǎn)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duì)級(jí)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guī)定。”因此,在買賣合同糾紛中,如當(dāng)事人之間已約定選擇了與爭(zhēng)議有實(shí)際聯(lián)系的地點(diǎn)的法院管轄,且不違背級(jí)別管轄和專屬管轄規(guī)定的,應(yīng)當(dāng)首先按其約定確定管轄法院。
二、“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地域管轄
《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修正)第二十條規(guī)定,“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交付標(biāo)的的,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通過(guò)其他方式交付標(biāo)的的,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duì)履行地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一)什么是“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
1. 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的界定
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并未對(duì)何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做出統(tǒng)一規(guī)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的條款編著的書籍對(duì)此提供了部分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上]》(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shí)施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辦公室編著,2022年6月版,第116頁(y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上]》(沈德詠主編,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訴訟法貫徹實(shí)施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編著,2015年3月版,第159頁(y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逐條適用解析》(杜萬(wàn)華、胡云騰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2015年3月版,第28頁(yè))均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案件規(guī)定》)中第二條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的界定,即“信息網(wǎng)絡(luò)”是包括以計(jì)算機(jī)、電視機(jī)、固定電話機(jī)、移動(dòng)電話機(jī)等電子設(shè)備為終端的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廣播電視網(wǎng)、固定通信網(wǎng)、移動(dòng)通信網(wǎng)等信息網(wǎng)絡(luò),以及向公眾開(kāi)放的局域網(wǎng)絡(luò),并認(rèn)為審判實(shí)踐中可以參照該“信息網(wǎng)絡(luò)”的概念,認(rèn)為通過(guò)上述媒介訂立的買賣合同,均可視為以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
然而,對(duì)于上述觀點(diǎn),司法實(shí)踐中在就個(gè)案是否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進(jìn)行審查時(shí),部分法官持有不同的觀點(diǎn)。
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級(jí)人民法院(2023)京02民轄終90號(hào)案。該案的觀點(diǎn)是《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案件規(guī)定》第二條規(guī)定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的定義,僅適用于人民法院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民事糾紛案件,并不包括基于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產(chǎn)生糾紛的案件。《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案件規(guī)定》第二條規(guī)定中關(guān)于“信息網(wǎng)絡(luò)”的概念不應(yīng)等同于《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條規(guī)定中的“信息網(wǎng)絡(luò)”,二者在保護(hù)法益、立法旨趣等方面相距甚遠(yuǎn)。《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條規(guī)定側(cè)重于保護(hù)在信息網(wǎng)絡(luò)虛擬不確定的情況下買受人權(quán)益受損時(shí)的程序利益,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管轄規(guī)則具有傾向性保護(hù)的特點(diǎn),為維護(hù)商事交易的平等秩序,其適用范圍應(yīng)嚴(yán)格限制。買賣合同的“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需要滿足“特定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平臺(tái)上發(fā)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臺(tái)上完成”的要件,即在特定的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面向不特定消費(fèi)者發(fā)布、展示產(chǎn)品,完成交易。如果只是將微信等作為協(xié)商的工具或者合同文本內(nèi)容轉(zhuǎn)發(fā)對(duì)方的載體和方式,該情形不具備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合同的特征。
筆者認(rèn)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編著的相關(guān)書籍對(duì)判斷個(gè)案是否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作出了相應(yīng)的指引,但其也僅是認(rèn)為“可以參照”《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案件規(guī)定》第二條中“信息網(wǎng)絡(luò)”的概念對(duì)個(gè)案進(jìn)行認(rèn)定。然而,基于以互聯(lián)網(wǎng)飛速發(fā)展導(dǎo)致的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形成的交易的多樣性、復(fù)雜性,司法實(shí)踐中不應(yīng)機(jī)械地套用《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案件規(guī)定》第二條的概念,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個(gè)案的實(shí)際交易情況進(jìn)行實(shí)質(zhì)性的審查、判斷,以避免出現(xiàn)法律適用錯(cuò)誤的情況。
2. 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常見(jiàn)的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買賣合同的類型認(rèn)定
(1)通過(guò)淘寶、京東等特定的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交易形成的買賣合同
隨著電商行業(yè)、網(wǎng)絡(luò)直播的發(fā)展與興起,通過(guò)淘寶等特定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形成的交易規(guī)模越來(lái)越大,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該類案件性質(zhì)的認(rèn)定較為統(tǒng)一。其中,部分法院的裁判觀點(diǎn)摘錄如下:
(2023)甘民轄77號(hào)案中,甘肅省高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是指出賣人將標(biāo)的物在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平臺(tái)上展示并發(fā)出要求,買受人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作出購(gòu)買承諾,雙方形成合意而訂立的買賣合同。根據(jù)原告牛某的訴訟請(qǐng)求及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理由,本案系因互聯(lián)網(wǎng)購(gòu)物引發(fā)的糾紛,屬于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糾紛。原告牛某主張其通過(guò)被告新某的服務(wù)平臺(tái)、以支付對(duì)價(jià)的方式從被告吳某處購(gòu)買游戲賬號(hào)后,被游戲賬號(hào)原出售方即被告王某修改密碼,導(dǎo)致其喪失對(duì)游戲賬號(hào)的使用權(quán),原告牛某遂針對(duì)游戲賬號(hào)出售主體、交易平臺(tái)、游戲開(kāi)發(fā)主體提起訴訟。”
(2024)蘇02民轄終138號(hào)案中,案涉交易系通過(guò)抖音商城進(jìn)行,江蘇省無(wú)錫市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定該案系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
(2024)粵01民轄終249號(hào)案中,廣州市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本案中,被上訴人通過(guò)閑魚(yú)網(wǎng)絡(luò)購(gòu)物平臺(tái)及微信交流,訂購(gòu)案涉車輛,約定通過(guò)貨運(yùn)配送,收貨地為廣州市增城區(qū),故案涉買賣合同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
(2022)京04民轄終25號(hào)案中,北京市第四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本院經(jīng)審查認(rèn)為,本案系裴俊濤通過(guò)淘寶網(wǎng)與東莞市大朗佳釀酒業(yè)商行簽訂的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糾紛。”
綜上,當(dāng)前司法實(shí)踐中,通過(guò)淘寶、京東等特定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與不特定消費(fèi)者之間產(chǎn)生的交易,因具備通過(guò)虛擬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發(fā)出要約、作出承諾并最終達(dá)成合意的特征,通常會(huì)被認(rèn)定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
(2)通過(guò)微信等通訊軟件進(jìn)行溝通、磋商、交易而形成的買賣合同
微信、QQ等通訊軟件帶來(lái)的便利性使得通過(guò)微信等進(jìn)行溝通、磋商、進(jìn)而形成交易越來(lái)越多。然而,司法實(shí)踐中,并非所有通過(guò)微信等溝通、交易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均被認(rèn)定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需要結(jié)合個(gè)案的情況進(jìn)行分析、判斷。其中,部分法院的裁判觀點(diǎn)摘錄如下,可作為參考:
(2023)最高法民轄66號(hào)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rèn)為:本案爭(zhēng)議焦點(diǎn)為案涉合同是否可以認(rèn)定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本案中,周志豪起訴主張其與澤航公司以微信聊天方式買賣貨物,但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對(duì)周志豪所作的調(diào)查筆錄記載,周志豪與澤航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林在案涉買賣發(fā)生前相識(shí),周志豪到澤航公司處考察后,吳林通過(guò)微信向周志豪報(bào)貨單,周志豪依貨單送貨。此后,周志豪還到澤航公司處催要貨款。從案涉買賣過(guò)程看,買賣雙方明確且相互知曉,微信僅是雙方溝通方式之一,案涉買賣合同的要約、承諾等訂立行為并非全部通過(guò)微信方式達(dá)成,故不宜認(rèn)定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應(yīng)當(dāng)按照一般合同糾紛確定管轄。
(2023)最高法民轄14號(hào)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rèn)為:本案爭(zhēng)議焦點(diǎn)為案涉合同是否可以認(rèn)定為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本案中,王有朋主張其與俞文權(quán)達(dá)成了黃沙買賣合同,并向開(kāi)發(fā)區(qū)法院提交了其與俞文權(quán)的微信聊天記錄予以證明。從該微信聊天記錄看,雙方未就案涉買賣簽訂書面合同,微信內(nèi)容主要為雙方就合同履行以及發(fā)生履行爭(zhēng)議后的溝通情況,微信內(nèi)容同時(shí)顯示雙方亦曾面談。可見(jiàn),微信只是王有朋與俞文權(quán)的溝通方式之一,案涉買賣合同并非雙方通過(guò)微信方式訂立。故案涉合同不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普通的買賣合同。
(2023)京02民轄終90號(hào)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交易主體具有虛擬性的特征,對(duì)該合同認(rèn)定的范圍不宜擴(kuò)大,應(yīng)僅限于具有典型信息網(wǎng)絡(luò)合同特征的“網(wǎng)絡(luò)購(gòu)物行為”,微信只是雙方傳達(dá)合同內(nèi)容的載體和方式,不具備信息網(wǎng)絡(luò)合同的典型特征。……在信息網(wǎng)絡(luò)高度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背景下,輔以微信等方式對(duì)買賣合同的相關(guān)內(nèi)容進(jìn)行確認(rèn),符合交易習(xí)慣及經(jīng)濟(jì)效益,不能僅以通過(guò)微信方式進(jìn)行了溝通、協(xié)商就認(rèn)定雙方之間達(dá)成的內(nèi)容屬于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同時(shí),《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條規(guī)定側(cè)重于保護(hù)在信息網(wǎng)絡(luò)虛擬不確定的情況下買受人權(quán)益受損時(shí)的程序利益。如果將微信上訂立的買賣合同一概納入“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范圍,從而確定買受人住所地或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則明顯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特別是當(dāng)出賣人主張支付貨款時(shí),其往往只能到買受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將極大增加維權(quán)成本。另外,買賣合同的“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需要滿足“特定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平臺(tái)上發(fā)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臺(tái)上完成”的要件,即在特定的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面向不特定消費(fèi)者發(fā)布、展示產(chǎn)品,完成交易。如果雙方只是將微信作為協(xié)商的工具或者合同文本內(nèi)容轉(zhuǎn)發(fā)對(duì)方的載體和方式,則此情形不具有信息網(wǎng)絡(luò)合同的特征。”此外,對(duì)于上述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構(gòu)成要件,(2024)遼14民轄終20號(hào)案中遼寧省葫蘆島市中級(jí)人民法院同樣持有該觀點(diǎn)。
(2024)冀06民轄終56號(hào)案中,河北省保定市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關(guān)于以微信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是否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實(shí)際情況予以認(rèn)定。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交易主體具有虛擬性的特征,對(duì)該合同認(rèn)定的范圍不易擴(kuò)大,應(yīng)僅限于具有典型信息網(wǎng)絡(luò)合同特征的“網(wǎng)絡(luò)購(gòu)物行為”。本案中,微信只是雙方傳達(dá)合同的載體和方式,并不具備信息網(wǎng)絡(luò)合同的典型特征,因此上訴人主張按照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確定本案的管轄法院,缺乏事實(shí)依據(jù)。
(2024)粵05民轄終9號(hào)案中,廣東省汕頭市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是指出賣人將標(biāo)的物在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平臺(tái)上展示并發(fā)出要約,買受人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作出購(gòu)買承諾,雙方形成合意而訂立的買賣合同。《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所規(guī)定的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管轄權(quán)劃分情形,其宗旨是在買受人接受產(chǎn)品的終端不具有確定性以及出售方出售產(chǎn)品的終端不確定的情況下,解決網(wǎng)購(gòu)消費(fèi)者難維權(quán)以及管轄法院不明確的問(wèn)題,本案中,在案證據(jù)顯示雙方當(dāng)事人系將微信作為雙方交易時(shí)磋商的工具,以微信方式商討合同細(xì)節(jié)、傳輸合同內(nèi)容,交易主體是特定的,且買受人及出賣人的終端也都是確定的,據(jù)此達(dá)成的交易不符合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的構(gòu)成要件,與一般買賣合同并無(wú)差異,應(yīng)當(dāng)以一般買賣合同糾紛確定管轄。
(2024)蘇02民轄終14號(hào)案中,上訴人主張“其是通過(guò)微信向林某購(gòu)買布料、匹數(shù)等,林某通過(guò)微信報(bào)價(jià),其表示無(wú)異議后便通過(guò)微信把收貨地址發(fā)送給林某(陸某),其通過(guò)微信向林某支付了貨款,林某通知物流方發(fā)貨,整個(gè)交易過(guò)程雙方并未簽訂書面買賣合同,在此買賣之前雙方并不相識(shí),故該買賣合同屬于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糾紛。”對(duì)此,江蘇省無(wú)錫市中級(jí)人民法院認(rèn)為:本案中,林某主張其與段某達(dá)成了買賣合同,并向一審法院提交了雙方之間的微信聊天記錄予以證明。從該微信聊天記錄看,雙方雖未就案涉買賣簽訂書面合同,但雙方就貨物買賣的標(biāo)的、數(shù)量、價(jià)款、交貨方式等的協(xié)商均已在微信中約定,故雙方成立“線上訂立、線下交貨”的買賣合同關(guān)系,應(yīng)以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
綜上,根據(jù)案例檢索情況可知,目前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通過(guò)微信等以通訊功能為主的軟件形成的交易,需要結(jié)合個(gè)案的交易過(guò)程、細(xì)節(jié)等進(jìn)行綜合判斷。整體而言,如通過(guò)微信等成立的買賣合同同時(shí)符合“特定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平臺(tái)上發(fā)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臺(tái)上完成”的要件(或是通過(guò)虛擬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完成發(fā)出要約、作出承諾并達(dá)成合意的),通常可以被認(rèn)定為系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而那些僅僅是通過(guò)微信聊天等方式就交易細(xì)節(jié)等進(jìn)行溝通的,往往被認(rèn)定為不具備“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特征。
(二)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區(qū)分
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訂立買賣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補(bǔ)充規(guī)定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高速發(fā)展、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進(jìn)行的交易激增的經(jīng)濟(jì)背景下而新增設(shè)立的,是為解決因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交易存在虛擬、不確定等特點(diǎn)而易導(dǎo)致的被告住所地通常難以被直接知曉、合同履行地難以確認(rèn)等問(wèn)題。因此,該條款實(shí)際上是在特定情況下針對(duì)買受人的傾向性保護(hù),通過(guò)對(duì)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履行地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側(cè)重保護(hù)在信息網(wǎng)絡(luò)虛擬、不確定的情況下買受人合法權(quán)益受損時(shí)的程序利益。
同時(shí),考慮到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交付方式的多樣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規(guī)定對(duì)不同形式的買賣合同的履行地進(jìn)行區(qū)分,即: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交付標(biāo)的的,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通過(guò)其他方式交付標(biāo)的的,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
而對(duì)于上述兩種交易的區(qū)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逐條適用解析》(杜萬(wàn)華、胡云騰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2015年3月出版,第27頁(yè))對(duì)此進(jìn)行了說(shuō)明:“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交付標(biāo)的的”形式為“線上交易、線上交付”,即線上交付數(shù)字化產(chǎn)品,如在電腦或者智能手機(jī)上購(gòu)買并下載應(yīng)用程序軟件等數(shù)字化產(chǎn)品等,該類合同的履行地為“買受人住所地”;關(guān)于“通過(guò)其他方式交付標(biāo)的的”交易形式,即指“線上交易、線下交付”,該類產(chǎn)品主要是實(shí)物產(chǎn)品,而實(shí)物產(chǎn)品不像數(shù)字化產(chǎn)品那樣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交付而難以確定收貨地址,因此將“收貨地”規(guī)定為該類合同的履行地。
同時(shí),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該補(bǔ)充規(guī)定依舊強(qiáng)調(diào)了當(dāng)事人約定優(yōu)先的原則,也即“合同對(duì)履行地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三、傳統(tǒng)買賣合同糾紛與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之地域管轄規(guī)定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
如前所述,在當(dāng)事人沒(méi)有約定管轄法院的情況下,對(duì)于已經(jīng)實(shí)際履行但沒(méi)有約定的履行地點(diǎn)的買賣合同,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對(duì)傳統(tǒng)買賣合同糾紛與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的合同履行地存在著不同規(guī)定。具體來(lái)說(shuō):
對(duì)于傳統(tǒng)買賣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修正)第十八條規(guī)定,“合同對(duì)履行地點(diǎn)沒(méi)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zhēng)議標(biāo)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動(dòng)產(chǎn)的,不動(dòng)產(chǎn)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其他標(biāo)的,履行義務(wù)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即時(shí)結(jié)清的合同,交易行為地為合同履行地。”
而對(du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修正)第二十條規(guī)定,“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交付標(biāo)的的,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通過(guò)其他方式交付標(biāo)的的,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
因此,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作為一種新形式的買賣合同,在確定其合同履行地時(shí),不可避免地會(huì)出現(xiàn)法律規(guī)則適用競(jìng)合的情形。司法實(shí)踐中,不同法官對(du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與第二十條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法院因此對(duì)該類案件的管轄認(rèn)定存在著不同的裁判結(jié)果,目前尚未形成統(tǒng)一法律適用規(guī)則。
而對(duì)于該特定情況下的法律適用,筆者認(rèn)為根據(jù)“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已對(duì)于“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的合同履行地作出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下,該特別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較《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一般合同糾紛的合同履行地的一般規(guī)定優(yōu)先適用。因此,在根據(jù)合同履行地確定以信息網(wǎng)絡(luò)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管轄法院時(shí),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的規(guī)定,以減少法律適用的差異,形成統(tǒng)一的裁判標(biāo)準(zhǔn),以便各方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中保護(hù)自身的程序利益。
四、結(jié)語(yǔ)
綜合上述,不同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對(duì)于信息網(wǎng)絡(luò)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的認(rèn)定均可能存在不同的觀點(diǎn)。因此,在訴訟過(guò)程中,基于不同的訴訟地位、訴訟目的等各方面因素的綜合考量,原被告雙方均可能做出不同的訴訟選擇。具體而言,原告在起訴時(shí)應(yīng)當(dāng)慎重選擇起訴的法院,避免出現(xiàn)法院不予受理或是被告提出管轄權(quán)異議后被法院裁定移送的情況,由此造成訴訟進(jìn)程的拖延;相反,被告在答辯期限內(nèi)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受訴法院有無(wú)管轄權(quán)、有無(wú)提出管轄權(quán)異議之必要,在特定情況下可減少訴訟成本的增加等。
律師介紹